【歷史上的今天——1027霧社事件(Mkuni Paran)】
2023年10 月27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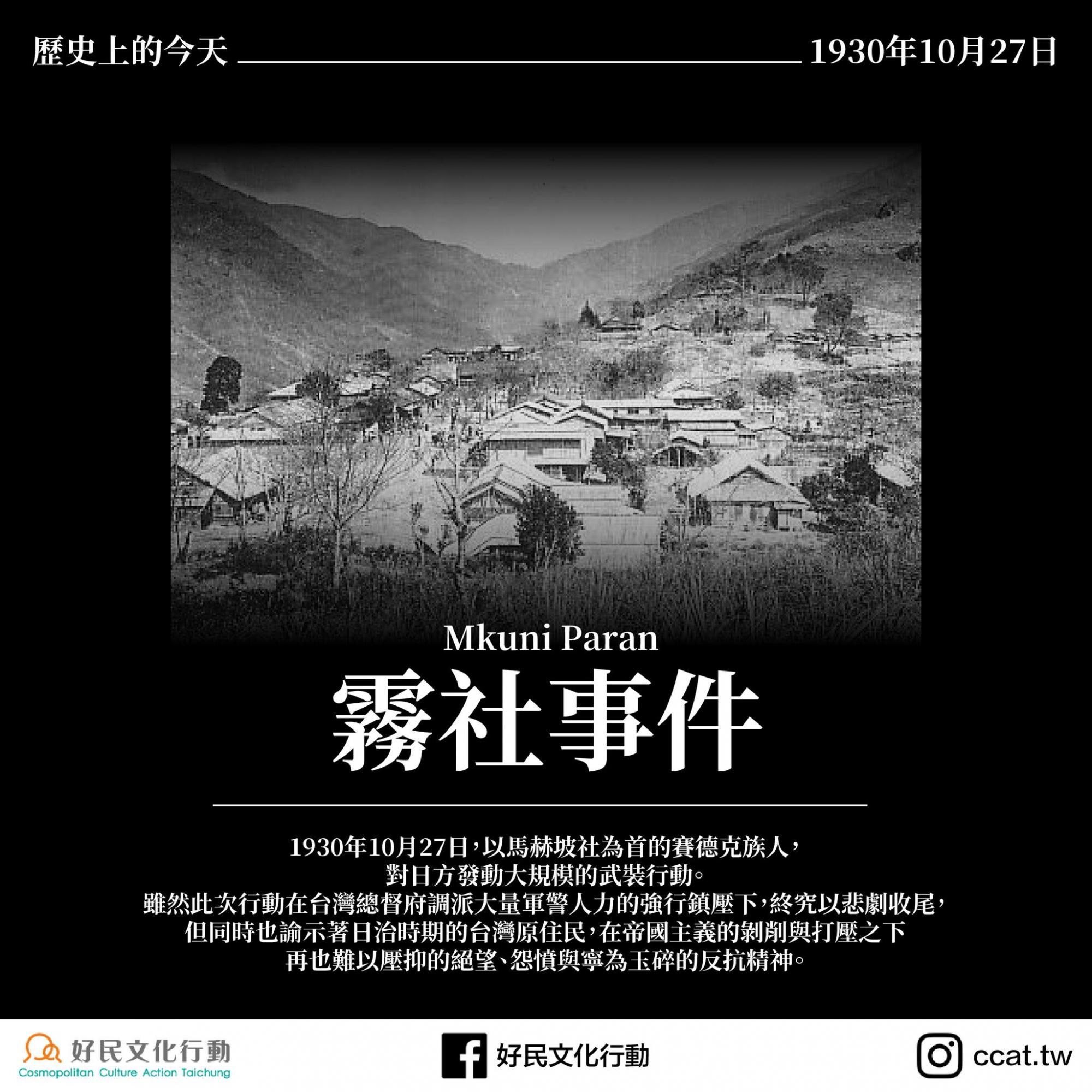
【歷史上的今天——霧社事件(Mkuni Paran)】
兄弟們!來!來!
來和他們一拚!
憑我們有這一身,
我們有這雙腕,
休怕他毒氣、機關槍!
休怕他飛機、爆裂彈!
來!和他們一拚!
兄弟們!
憑這一身!
憑這雙腕!
——節錄自 賴和/南國哀歌
台灣進入日治時代以後,現代化的腳步在殖民政權的驅策下愈發變得急湊。殖民地的一切資源,都納入帝國的管轄,被任意分配、取用;殖民地上的所有人民,也都被帝國所管理與指揮。於是,過去清朝政府始終難以完全涉入的台灣原住民的生活領域,在更換政權之後,也開始被更加積極地介入,就此演變成日治時代初期,原住民部落和殖民政權之間,所產生的一連串或大或小的衝突事件。
在這些衝突的過程當中,有些人因為沒辦法接受殖民政權的高壓統治,繼而選擇起身反抗,也有人因為顧及部落全體的安危,因此選擇妥協——但我們也知道,人就算在一時之間選擇了妥協,若是被打壓到難以勘受的地步,也還是有可能撒手一搏,甚至做出更劇烈的反彈。
其中霧社事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所產生的悲劇。
霧社位於台灣的中部山區,而在當地有賽德克族人共十餘個部落,分布於霧社台地。日治時代初期,霧社亦是台灣總督府開發山林礦產資源的重要地區,因此時常與居住於此處的賽德克人產生衝突,更曾發生過一整批探勘隊遭到攻擊全滅的事件。雖然在日方以武力鎮壓、經濟封鎖等手段的雙重威逼下,賽德克人一度也只能忍辱吞聲,維持順從屈服的態度,然而在這樣的一種順從之下,長期累積壓抑的族群衝突卻依然存在。
由於台灣總督府積極介入原住民的生活,以「現代化」的名義,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與文化習俗,包含禁止原住民持有槍械,禁絕原住民的傳統習俗,管制部落內的民生物資原料,強迫原住民承擔工程勞役,嚴重影響到部落原本透過農獵等生產方式所取得的收穫。
另一方面,許多日本人又對失去傳統生計方式,因此只能轉行擔任底層勞工的原住民進行歧視與虐待,更發生薪資發放不實的狀況。此外,由日方所鼓勵的聯姻政策,也因為文化差異等因素,讓不少部落的婦女也受到傷害,這樣的婚姻往往都只能以悲劇收場。
綜合而言,無論是固有的社會制度、經濟活動、語言與文化習俗都處於弱勢地位,受到帝國主義的剝削與打壓,長久以往形成不少部落成員對殖民政權的怨憤與不滿。
隨著雙方的衝突越演越烈,到了1930年10月07日,馬赫坡社更發生了一起「敬酒風波」,起因是部落內舉行婚宴的過程中,頭目莫那魯道(Mona Rudo)的長子達多莫那(Tado Mona),原本要與當地駐村的警察吉村克己敬酒,不料卻被吉村嫌棄為「不潔」,甚至遭以警棍毆打,雙方因此發生鬥毆事件。
這個事件的發生,終於引爆賽德克人長期的積怨,最後演變成聯合其他各部落所發起的武裝行動。
1930年10月27日的凌晨,賽德克人先將馬赫坡社的駐警殺死,隨後沿路襲擊駐在所,往霧社前進。在抵達霧社之後,賽德克人開始針對警察分室、郵局、官員宿舍等多處進行攻擊,並於 #霧社公學校 砍殺當天前來參與運動會的日籍官員、來賓以及學童。其後,賽德克人也持續攻擊霧社周邊的駐在所,並且切斷對外聯絡的電話線路與輕便鐵道。
事件發生過後,台灣總督府也緊急調派台灣各地的軍警人員,並在10月31日對各個起義部落開始發動攻擊,雙方對峙數日,最後日方將賽德克人逼至馬赫坡岩窟,並以砲擊、飛機投擲炸彈等方式對僅存的賽德克人進行圍攻,期間更投擲違反國際公約的白磷燃燒彈,以及發射路易斯毒氣彈。
由於在起事之際,農作尚未收穫,部落也在後來遭到攻佔,陷入糧食不繼的問題的賽德克人很快就縮小了對日反抗的活動規模及組織,許多部落內的婦女、兒童,在過程中就已經遵循傳統選擇自縊,其他人則在後來向日方投降。起事者如莫那魯道,也在將妻子、孫子的後事安排妥當後,隱入深山,飲彈自盡;其長子達多莫那,與其所帶領的數名勇士,在拒絕勸降之後,也於山中自縊。
根據後來的統計,參與霧社事件的數個部落,共計一千餘人,在日方與賽德克人的交戰下,死於刀槍、飛機與砲彈轟炸者共計三百餘人,自縊身亡者亦有將近三百餘人,遭受俘虜者共計兩百餘人,投降者共計五百餘人,在事件過後被收容於霧社。然而,隔年的04月25日,在日方的縱容之下,這些受到收容的賽德克人,又遭受到其他親日部落的屠殺,也被視為「第二次霧社事件」,事件後僅存的兩百餘人被遷移至 #川中島,仍然持續遭到日方的秋後算賬而被逮捕或者失蹤。
霧社事件發生之後,在台灣本島內外都引發巨大的輿論。
其中蔣渭水所領導的臺灣民眾黨,透過《臺灣新民報》追蹤、報導事件,同時設置民意專欄,交流各方意見,而臺灣民眾黨以及臺灣自治聯盟等以台灣漢人作為主體的政治組織,也對此一事件發起抗議活動。
臺灣民眾黨向日本內閣發送電報,揭發台灣總督府對原住民所進行的剝削、打壓,因此造成霧社事件悲劇的發生,並以此提出相關改革之訴求,又更進一步向國際聯盟提出控訴,抗議日本殖民政府以毒瓦斯屠殺台灣的原住民。
這一連串的抗議行動使日本內閣不得不正視台灣所發生的問題,台灣總督石塚英藏、總務長官人見次郎 遭到撤換,警務局長石井保、臺中州知事水越幸一 也跟著去職。雖然繼任的日籍官員一度改採懷柔政策,試圖平息此次事件的餘波,但是新任的總務長官高橋守雄,仍然在發生了第二次霧社事件之後去職。
台灣漢人的最後一起武裝對日反抗行動,是發生於1915年的噍吧哖事件,在此之後,台灣漢人開始改以推廣文化運動、議會設置請願等方式,與殖民政權展開長期的對峙;然而在另一方面,受到更嚴重的欺凌、打壓與剝削的台灣原住民,在被逼迫到難以容忍的處境下,他們選擇以更加悲壯、更慘烈,也更加義無反顧的方式,向殖民政權發出了不願再繼續屈從的怒吼。
***
定期定額捐款,文化建國鬥陣來!
最棒的台派活動在好民!
立刻成為好民之友➡https://tinyurl.com/yc5xr4h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