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今天——0804鍾理和逝世】
2023年8 月03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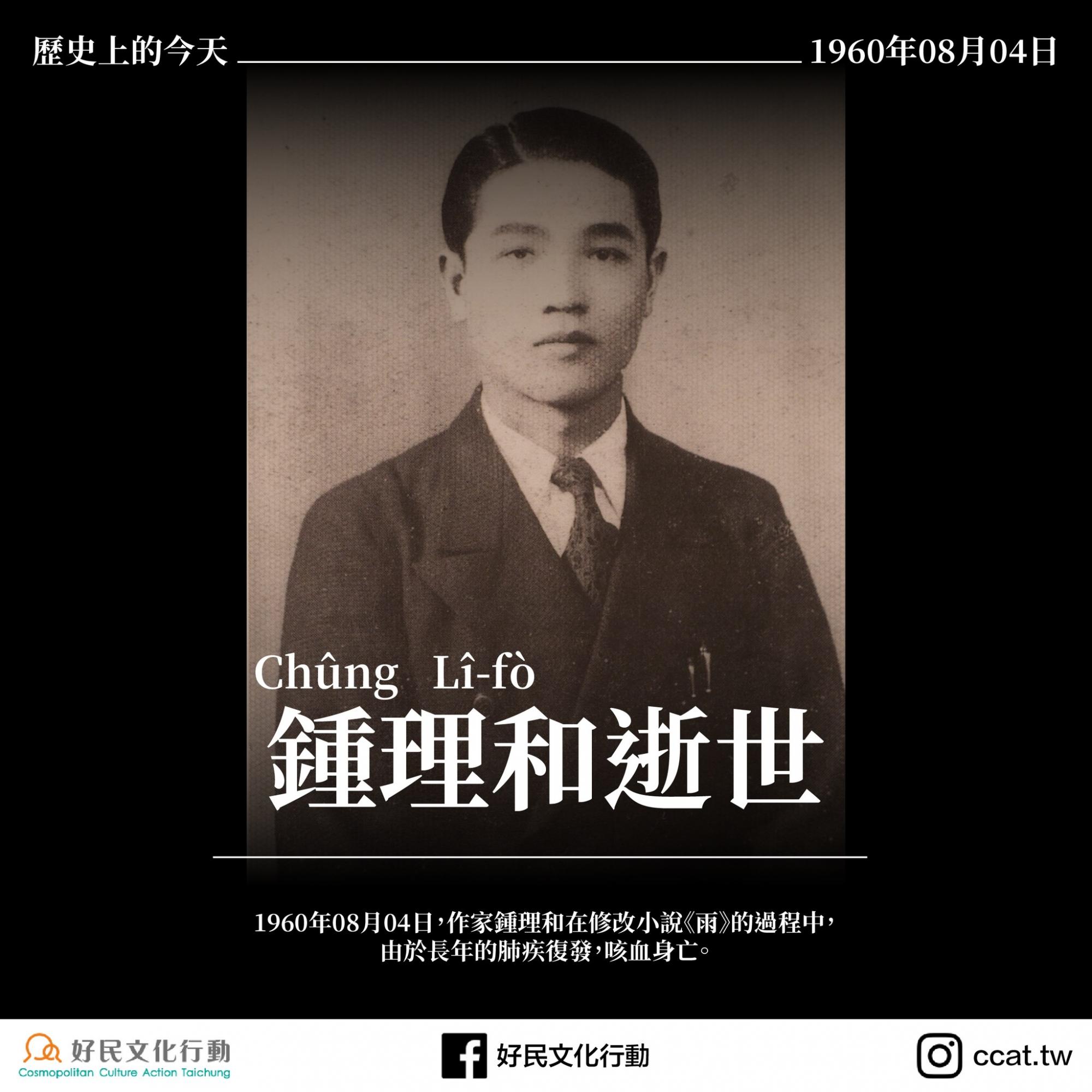
【歷史上的今天——鍾理和逝世】
鍾理和(Chûng Lî-fò),1915年12月15日出生於阿緱廳大路關庄的新大路關(今屏東縣高樹鄉廣興村)。
鍾理和出生於家境相當富裕,他的祖先不僅是當時新大路關的開闢者之一,其父親鍾鎮榮也是當地有名的地主與企業家。1895年清國割讓台灣,鍾鎮榮由於對殖民統治感到不滿,遂將姓名改為「鍾蕃薯」。
鍾蕃薯娶了數名妻子,其中鍾理和與同父異母的弟弟鍾和鳴,兩人後來一同進入鹽埔公學校就讀,並利用放假期間,於私塾學習漢文。從鹽埔公學校畢業之後,鍾和鳴進入高雄州立高雄中學繼續升學,然而鍾理和因為體檢不合格,沒辦法報考,遂轉而就讀長治公學校高等科,並且繼續接受私塾的漢文教育。這段期間,他受到私塾老師光達興的影響,開始嘗試寫作。
1932年,鍾理和結束了私塾的學業,這時鍾蕃薯與其友人合資,買下了美濃尖山的土地,並前往開拓經營,後來鍾蕃薯更帶領家人遷往此處,鍾理和也就隨同前往,協助父親的事業。但事實上,比起性格務實的父親和兄長,鍾理和對於藝文類型的活動有著更濃厚的興趣,他曾經向家人要求前往日本學習繪畫,卻遭到否決。
當時,美濃尖山的農場僱請了大量的工人,而鍾理和也就在跟這些工人接觸的過程中,認識了前來做工的少女鍾台妹,但由於兩人姓氏相同的關係,在過去被認為是婚姻的禁忌,鍾理和和鍾台妹的戀情,也就受到極大的阻攔。
無論是求學、志願甚至是愛情都被家人否決的鍾理和,在1940年08月,帶著鍾台妹私奔離開了家鄉。他們一路輾轉來到當時滿洲國的奉天(今中國瀋陽),又在隔年帶著初生的長子鍾鐵民遷居至北平(今中國北京)。
居住在北平的期間,鍾理和一邊從事各種工作賺取家用,一邊持續寫作,並且接受友人的接濟,而這段旅居在中國的歲月,後來也在他的筆下成為《夾竹桃》這本小說合集,鍾理和以一名對中國「原鄉」懷抱熱血情感,到後來理想幻滅的台灣青年的視角,用尖銳直接的筆觸,描繪自身對於「原鄉」的矛盾情感。
這樣的矛盾情感的延續,也在他的作品《原鄉人》以及《白薯的悲哀》裡可以看到。鍾理和以「白薯」來比喻臺灣人,面對戰爭的結束,看似已經脫離殖民政權的統治,「回歸祖國」,所面對的卻是依然揮之不去的疏離,甚至是唾棄、輕視與排斥。
而相當特別的是,有別於描寫日治時期的台灣經驗的作家們,鍾理和則是作為在「異鄉」的台灣人,來描寫他所感受到的孤獨與艱困,而作為一個台灣人,這樣的經驗也就顯得更加複雜而糾結了。
1946年,鍾理和回到了台灣,面對的是戰後殘破的故鄉,以及不復往日繁榮的家園,父親鍾蕃薯也已在數年前去世。
他應聘至屏東縣內埔初中擔任代用國文教員,後來也曾在弟弟鍾和鳴(當時已改名為鍾浩東)的邀請下,前往擔任基隆中學的總務主任。但這段期間,他已經被診斷出確診肺炎,也因為疾病反覆地發作,不得不辭去工作,更在治療的過程中不得不變賣土地,籌措醫藥費。
後來鍾理和動了胸腔手術,取走了六根肋骨,雖然病情得以穩定下來,身體卻變得過度虛弱而無法進行一般的勞動。
這段期間,在基隆中學擔任校長的鍾浩東,也因為其過去對國民黨的失望,轉而傾向左翼的政治立場遭受逮補,在馬場町被槍決。回到家鄉的鍾理和,在重新思考過寫作的方向之後,轉而而開始觀照社會基層的人情百態與地方風土,他繼續勤於筆耕,並四處投稿作品。
1955年,鍾理和將他所完成的長篇小說《笠山農場》投稿至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小說中的「笠山農場」,事實上正是以美濃尖山的農場作為藍本,所寫下的帶有濃厚自傳色彩的作品。
隔年,《笠山農場》獲得國父誕辰紀念獎第二名,首獎從缺;但是同年年底,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的停辦,導致《笠山農場》無法出版,鍾理和花了好長一段時間才要回原稿,在尋找其他出版機會時也不甚順利。
1957年,鍾理和加入了鍾肇政的《文友通訊》,開始與台籍的作家建立起連結,而在作家們的幫助以及林海音於《聯合報》副刊擔任主編的期間,他的作品比較頻繁地獲得了刊登的機會。
然而,1960年08月04日,鍾理和在修改小說《雨》的途中依然因為肺病復發,咳血身亡。
葉石濤曾評論鍾理和的小說:「一向不以社會性觀點來處理題材,倒用美學和人性來安排情節,使得他的小說細膩動人具有極高度的藝術成就。」
從過去自我認同的掙扎,到對鄉土的觀照,鍾理和將生活中所遭遇到的苦悶與艱辛融入到他的文學裡,卻不再做憤怒的反擊,或者兀自沈浸在悲傷愁苦的情緒中無法自拔,反而是以樸實的文字,真摯的情感,來譜出他對生命最深刻的表白。
***
【為台灣民主儲值】定期定額捐款,文化建國鬥陣來!
最棒的台派活動在好民!
立刻成為好民之友➡https://tinyurl.com/yc5xr4h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