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今天——0714廣電法針對「方言」之設限解除】
2023年7 月11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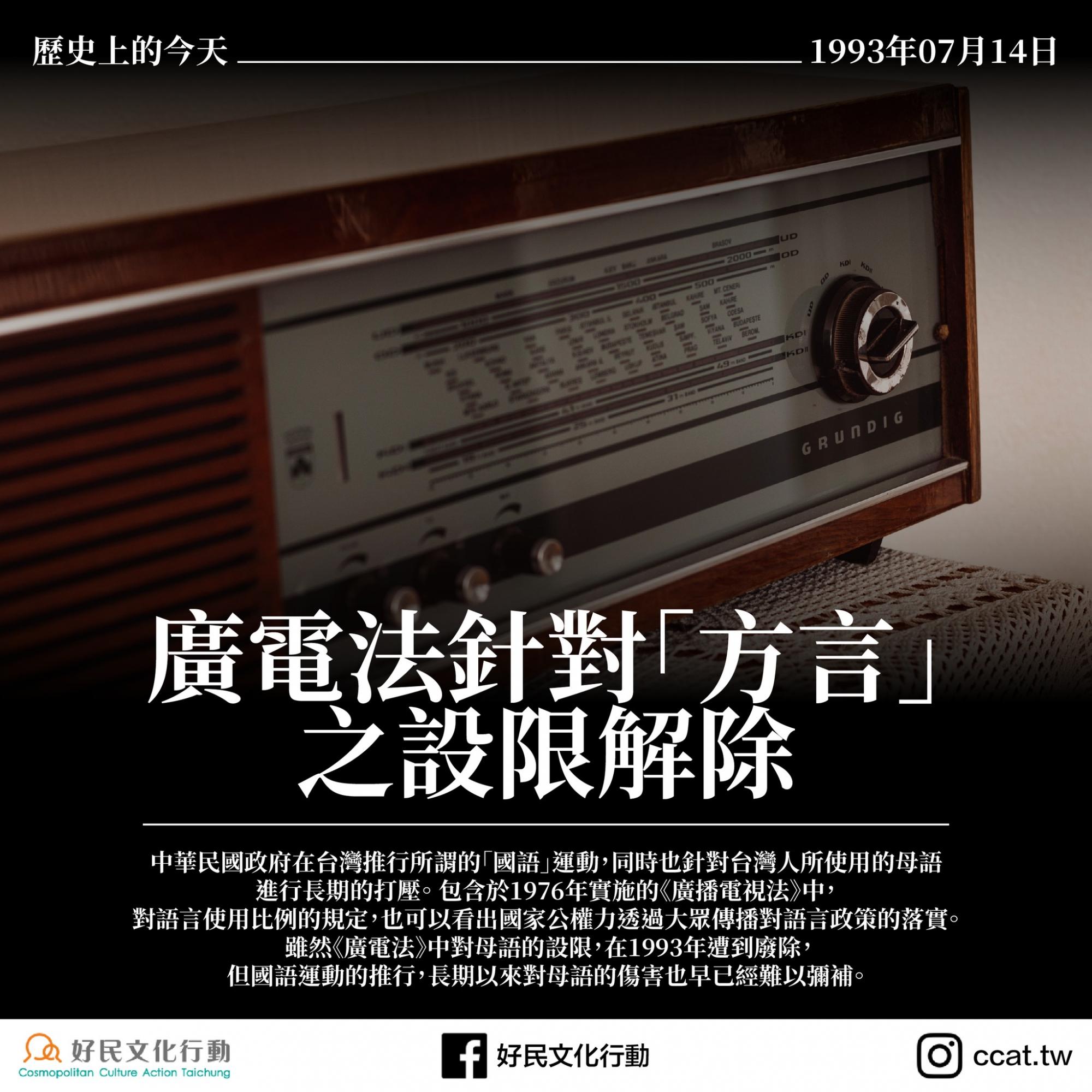
【歷史上的今天——廣電法針對「方言」之設限解除】
二戰結束後,中華民國政府來到台灣,並於1946年04月02日成立「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推行所謂的「國語」——常被通稱為「北京話」的華語,一方面力圖「增強國家民族意識」,立即性地禁絕當時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對日語的使用習慣,另一方面,也對台灣人本來在使用的母語,進行更全面且更長久的打壓。
1956年,為了使國語的推動更加普遍,台灣省教育廳於是規定,各機關學校以及公共場所內一律只能使用國語,並禁止使用被政府當局視作「方言」的母語,斗大的標語「我要說國語不說方言」的宣導牌,被掛在學校教室外,許多教育單位甚至鼓勵學生互相監視,一旦抓到說母語的孩子,則祭出罰錢、罰寫等懲處,甚至是掛上狗牌,當眾羞辱。
然而當時在台灣的基層社會裡,台語的使用依然相當普及,包含廣播、電視、電影等大眾傳播媒介,台語的客群依然不小。
隨著電視開始在台灣社會普及,台視、中視、華視三家電視台為了競爭廣告主與收視率,更從原本僅一家台視播放華語節目的情形,改變為讓台語節目也開始在電視上播送,諸如布袋戲、歌仔戲、連續劇等,獲得了頗高的收視率——但這也嚴重妨礙到政府當局對於國語運動的推行。
1972年,教育部文化局開始針對電視台播送的台語節目祭出規定,限制電視台每天播出的台語節目時間,而國民黨內部也提出審查台語節目劇本的要求,並且屢屢刁難,不予通過。
1973年,自教育部接手廣播、電視、電影業務的行政院新聞局,更開始制定《廣播電視法》,並於1976年實施,其中《廣電法》20條,即針對國內的廣播節目,明文規定「應以國語為主,方言應逐年減少」;另外有關於電台頻道、電視節目中國語的使用比例,也有明確的規範。
1980年,時任行政院新聞局長的宋楚瑜,更曾經明確指示,雖然《廣電法》20條的規範未能立刻嚴格執行,但各電台仍「惟自將注意此一規定,以期逐漸朝向此一長遠目標努力進行。今後各電台方言節目將逐漸減少,到全部以國語播出為止。」
政府當局利用公權力對母語的扼殺,由此可見一斑。
隨著1987年解除戒嚴,《廣電法》對母語的限制開始受到質疑與抗議,例如1988年12月28日,由黨外人士所發起的還我客家話運動(還我母語運動)等。
而《廣電法》20條之內容,也在1993年07月14日於立法院表決通過之後廢除,各家電視台、廣播頻道自此可以自行決定播送語言的使用比例。
然而,法條更改了,社會大眾的慣性思維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立刻改變的。
推動「國語」政策的另一面,就是對母語的排擠,而長期國語運動的推行,也產生了許多潛移默化的影響。
過去,許多家長會以自家孩子能說出一口標準的華語而感到驕傲,對於只會說母語的人則大為輕視;荒謬的懲處制度,進而也讓人產生「說母語會被處罰,因此是錯誤的、羞恥的」的扭曲認知,因此對說母語產生自卑感。
雖然《廣電法》不再對母語播送進行限制了,可是在大眾傳播的內容裡,依然反映著對母語的歧視——說台語的人多半是反派或是等待被救助者,而曾經為了適應新政權設下的新環境,而努力練就的「台灣國語」,分明是時代的悲哀,到了許多人口中,卻成為笑料的來源。
即便是解嚴之後出生的孩子,在此種環境的影響下,依然有一大部分的人認為說母語是「落伍的、俗氣的」,進而抗拒學習母語,錯過了語言學習的黃金階段,到後來要回頭補課時,已經相當困難。
甚至,當人們依舊不願放棄,試圖保存母語,進一步想要以文字的形式做更加系統化的整理時,還要忍受各種基於無知而生的冷嘲熱諷。
《廣電法》20條的廢除,是一種亡羊補牢的止損,但遺憾的是,中華民國政府長期以來對母語加諸的傷害,恐怕早已經難以彌補。
***
【為台灣民主儲值】定期定額捐款,文化建國鬥陣來!
最棒的台派活動在好民!
立刻成為好民之友➡https://tinyurl.com/yc5xr4h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