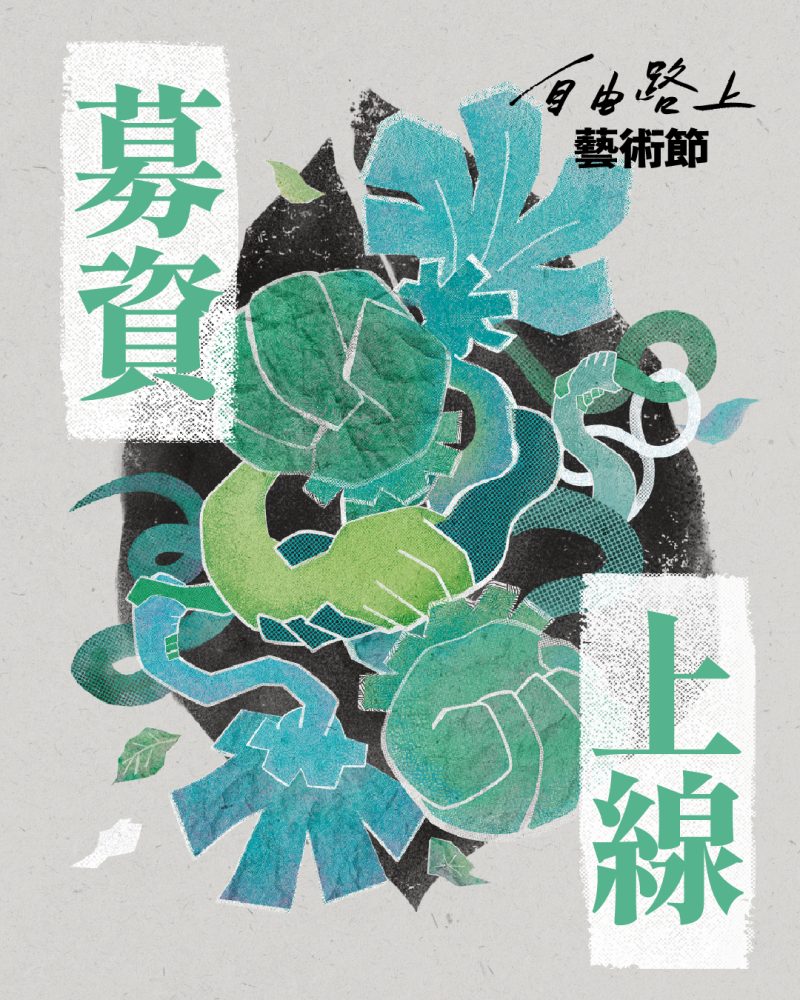10.05【好國好民講座】《聽海湧》之後──二戰台籍日本兵的真實歷史|活動側記
2024年10 月17日近期公視播映迷你劇集《聽海湧》,以二戰時期台籍日本兵被派至南洋擔任戰俘監視員的歷史為劇情主軸,引起許多討論與關注這段鮮少被提及的歷史。本次講座榮幸邀請到現為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的陳柏棕助理研究員,研究員本身長期從事二戰時期台籍日本兵的歷史研究,多年查探並訪談許多當事人做成口述歷史,與我們分享許多珍貴的史料與口述影像。

講座開頭,講者陳柏棕先概述台籍日本兵的狀況。當時大多數的台灣人是以軍夫、軍屬身分被派遣出去的,並非正式軍人。台灣人的派遣地點依當時日軍戰事發展而有所不同,譬如1937年日本與中國在上海開戰,便有台灣人被派去上海支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則有大量台灣人被派往南洋。當時台灣人被派遣的地點非常廣泛,稍近的有中國、香港、日本、朝鮮、菲律賓,最遠則至所羅門群島、新幾內亞、印度洋中的小島等。
「因為是敵前登陸,我們在離岸幾百公尺的地方就要下船,大家穿著救生衣,會游泳的要幫忙推不會游泳的人前進。」「日本人說我們台灣人很勇敢,在戰場上送物資,上頭子彈『咻──』『咻──』飛來飛去都不會怕。」口述影像中,不同前輩描述自己到中國從軍的經歷。講者說明,台灣人最初並沒有接受正規軍事訓練,才會發生在登陸時卻有不會游泳的人;甚至在戰場上根本不知道頭上的是子彈,自然也不知道要害怕。
前往戰場的不僅有男性,還有一群到香港、中國陸軍醫院擔任看護助手的女性,1942至1944年共有870人參與。講者訪談的幾位阿嬤,她們從軍的理由各自不同,有的人是認為家中兄弟早晚也會去當兵,去擔任看護助手或許可以照顧他們,更可以幫助家中經濟;有的則是認為在台灣只能結婚生子,難有作為,寧願把握機會到海外闖闖看;更有阿嬤寫下血書表達擔任看護助手的意願。從這些女性身上,能看見她們不甘於命運,勇敢掌握主控權的精神。
二戰後期日本逐漸敗退,為了扭轉戰局,派遣大量台灣人前往南洋戰線負責管理戰俘、生產糧食,以及建設機場等工作。許多人在南洋的經歷非常痛苦,在講者播放的口述影片中,被派往新幾內亞的黃春年前輩敘述:「事實上我到那裡時日本人幾乎都死光了。美軍先轟炸三日、海上艦砲射擊,之後才登島。我們退到第二陣地,伍長、軍曹、曹長接連出去都沒有再回來。最後只剩下我跟隊長,他說接到玉碎命令,要戰到死。」講者補充後續,後來黃春年前輩並沒有與美軍決戰,但隊長認為自己身為日本人還是要負起責任,在與美軍決ㄧ死戰前,請他代為轉告家屬自己死於何時何地,卻沒有留下住址,黃春年前輩因此無法將隊長的死訊告知其家人,一直耿耿於懷。
台灣人在南洋戰線的處境十分悽慘,除了不斷遭受轟炸與圍堵,也面對糧食、醫療用品的短缺以及疾病蔓延。有不少台灣人經歷過「吃人肉」的場景,看著戰友屍體的大腿、屁股肉消失,甚至自己差點也成為食物。講者播放曾在菲律賓從軍的林正興前輩的口述影像做總結:「回想那段經歷,晚上都睡不著。當時除了沒東西吃,為躲避戰機轟炸只能在晚上行動,在黑暗中抓著走在前面的人的行李走了一整夜,累到不能再累了。到後來我們心裡都在祈禱,如果上天要讓我死,拜託讓我的頭或肚子中彈,不要打中手或腳。頭或肚子中彈一下子就死了,但如果是打中手或腳,不知道要哀嚎幾天才會死。我們沒有人覺得可以活著回來。」
然而戰爭結束,並不代表苦難結束。台灣人在戰後變成「中國人」,台籍日本兵在二二八事件時被貼上標籤,被視為「日本的鷹犬」,遭遇長期的監控。但他們並不因此成為被動的他者,而是嘗試與自我進行連結。許多台籍日本兵以同學會、神明會等名義成立戰友會,彼此聯繫、與日本戰友交流。
在《聽海湧》的最後,阿輝在上絞刑台之前對志遠說:「回台灣以後要好好生活。」講者陳柏棕說現實中,許多二戰的遺族根本沒辦法好好生活。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兒子、丈夫、兄弟、父親究竟在哪裡戰死、甚至連生死不明。有的家屬一生都在追求答案,想知道親人到底發生什麼事,甚至期待會不會跟Suniuo(李光輝)一樣只是躲在叢林裡許多年,要把他接回家裡享福。
講座最後,講者提及歷史的複雜性,呼籲我們需跳脫二元思考去看見其中的異質性,看見人們做出不同選擇的能動性。隨著時間推移,那些記憶將一點一滴的消逝,講者邀請大家一起關注這些事情,一起留住他們的歷史。
這是一場既紮實又真實的講座,講者透過豐富的史料文獻為基礎,整理出台籍日本兵的樣貌,更透過口述影像的紀錄,讓我們能夠從當事人的口中得知他們的親身經歷。正如同講者說「我們不知道的事太多了」,透過這些歷史研究,我們才能得知曾經發生才台灣人身上的事情,甚至製作成戲劇引起更多人的關注。我們必須挖掘、記得這些歷史,並記取歷史帶給我們的教訓,絕不重蹈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