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今天——0420|葉永誌事件】
2025年4 月17日撰文:青台派志工|佳彣
「玫瑰少年在我心裡,綻放著鮮艷的傳奇,我們從來都沒忘記。你的控訴沒有聲音,卻傾訴更多的真理,卻換醒無數的真心。」——蔡依林的《玫瑰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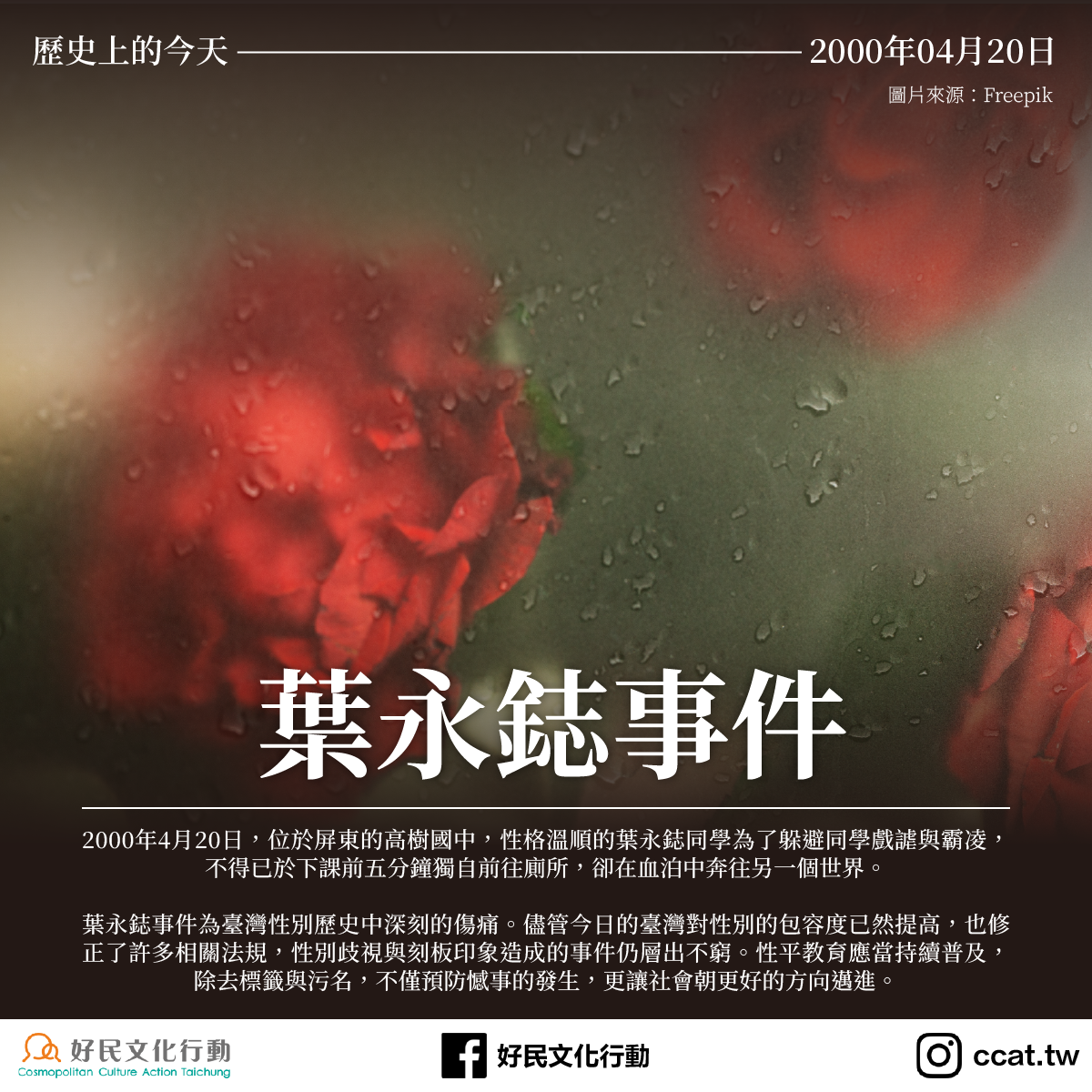
耳熟能詳的《玫瑰少年》中,不單單是描繪出接納各個性別的願景,更道出了二十五年前,一位少年的故事:2000年4月20日,位於屏東的高樹國中,葉永鋕同學於下課前五分鐘獨自前往廁所,卻在血泊中奔往另一個世界。針對此事,調查結果為:葉永鋕因意外(自身疾病、腳滑等因素)跌倒導致顱內出血,故身亡於廁所中。然而,這並非葉永鋕死亡的「原因」,而是死亡「過程」。
好端端的少年,為什麼會倒於血泊中?根據陳君汝(葉永鋕母親)描述,葉永鋕性格溫順、乖巧,好編織與烹飪,而這些性格與興趣,皆是屬於「女性的」、「陰柔的」,與葉永鋕的生理性別並不相符。小學三年級時,老師甚至要求陳君汝帶葉永鋕去看醫生,因其所作所為過於陰柔,太像「女孩子」。正因如此,葉永鋕自小便經常遭同學戲謔、霸凌、「驗明正身」等,為了躲避同學的攻擊,他便習慣在下課前五分鐘前往廁所。陳君汝得知此情形後,除了向校方理論外,也會要求兒子要「忍耐」、「勇敢」。
當年保守的社會氛圍,畫分出陰柔/陽剛的分野,並依個體的生理性別將其嵌入,而葉永鋕——生理男性配上陰柔性格的存在,挑戰了原先不可撼動的二元劃分。因此,為了維護秩序與權力的正當性,自然要將挑戰者歸類到「異常」的範疇之中。
當時葉永鋕的同學不單是作為霸凌者,更是符合社會標準的一群人,故可說是權力的持有者——他們與他。此對立具有權力的階序性,更有著葉永鋕作為「他者」,被社會排除的意味。由此可知,葉永鋕不單單是在「學校」之內遭到排擠,在更大的脈絡中,他仍然是遭到排除的一員。葉永鋕事件為臺灣性別歷史中深刻的傷痛,但無論是往昔或是現在,千萬個如同葉永鋕的存在,都已然殞落或處於掙扎之中。
回看當下,今日的臺灣經過歷史教訓與許多前輩的爭取後,對性別的包容度已然提高,也修正了許多相關法規。不過,原先鮮明的歧視或刻板印象,卻轉化為幽微的權力關係,在社群媒體、個體間的互動中等場域發生。因此,性別平等教育應當持續普及,除去標籤與污名,不僅預防憾事的發生,更讓社會朝更好的方向邁進。
葉永鋕事件帶動性別相關法律的推進,我們應當以史為鑒,共創更加包容、更具有性別意識的世界。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