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15【「新生」桌遊互動體驗】活動側記
2025年4 月08日「誣陷他人固然沉重且令人愧疚,然而時代背景使然,為了生存我們別無選擇。」──《新生》桌遊參與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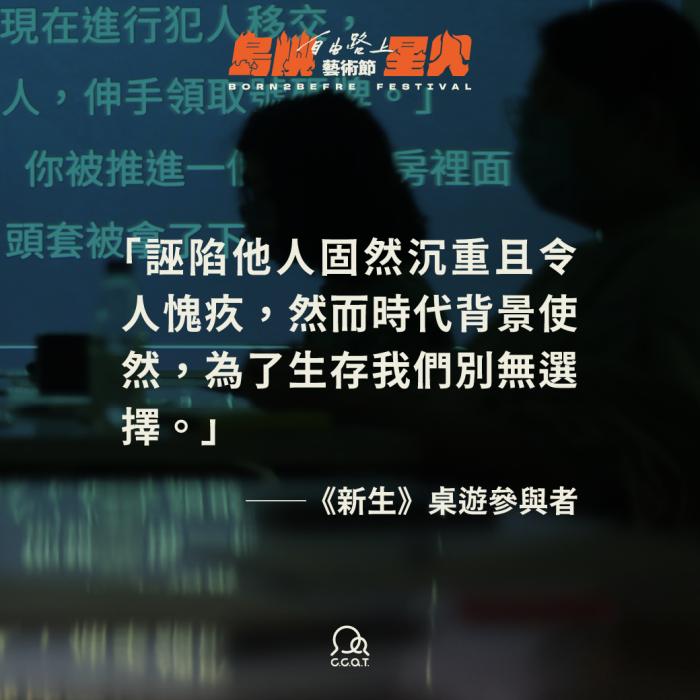
圖文編排:志工怡君
側記撰文:志工孟妍
本場活動藉由體驗國家人權博物館推出的桌遊——《新生》,邀請大家一同進入白色恐怖的肅殺情境中,扮演政治犯,齊心面對一連串的偵訊與審判。
遊戲開始,六位政治犯都有各自不同數值的體力、精神力,在遊戲推進的過程中,罪證將不斷增加,政治犯的身心狀況也越來越差。為了在人人自危的牢獄中存活,他們必須付出一些代價……
擲骰體會「新生」命運:不得已踏上審判之路
在只餘鐐銬碰撞聲的黑暗中,玩家化身為犯人們,被送到舊稱為東本願寺的保安處看守所,關押在狹小悶熱的單人牢房中。
在此地,犯人們將經歷辣椒水、疲勞轟炸、藥物注射的煎熬。政治犯們若不想就此認下罪行,只能投擲骰子決定自己會損失什麼,可能是體力、精神力、也可能屈打成招,在經歷酷刑後認罪。等到遊戲階段來到了藥物注射,艱難的選擇才真正開始,玩家可以檢舉他人,換取自己的安全;也可以堅守原則,不牽連他人。
活動安排在每個關卡邀請志願者上台體驗特務偵訊的過程。雖然模擬體驗的感受非常輕微,許多上台體驗的玩家仍感到恐懼,一片漆黑中只能聽見偵訊人員的恐嚇,以及模擬道具營造的不安與惶恐,即使沒有真正的肉體疼痛,也足夠折磨人心。
撐過東本願寺的折磨後,政治犯們隨即被移送軍法處看守所。在空間嚴重不足的牢房,連躺下睡覺都是奢侈,空氣不流通且人口過密的情況下,疫病很快開始蔓延,然而配給藥物供不應求,有的組別選擇出賣獄友以換取藥物,亦有部分組別不願為此牽連無辜之人。克服致命疫病不久,牢房來了新獄友,相處一段時間後,這位獄友卻要求你說出其他人的身家背景,以向長官檢舉,若是不配合,你也將被檢舉。到了這一回合,許多組別選擇檢舉他人換取減刑機會,確保能落實遊戲目標──活下來。
遊戲即將步入尾聲,在特殊事件中,六個組別共同投票決定是否逃獄,若全數同意則開始逃獄,若有人不願逃獄,選擇逃獄的組別罪證將會增加。然而無論是筆者親身體驗的遊戲回合,或是活動當日,三次的遊戲投票結果皆是不逃獄。不逃脫的組別認為無法確認大家團結與否,但為了存活不得已而變得多疑,經不起背叛,更不敢冒險;願意逃獄的組別則認為,在獄中的生活甚至較死亡可怖,逃出生天或盡快解脫都是更好的選擇。
角色各有原型:自遊戲回望歷史與政治受難者
最終的審判很快來臨。存活的政治犯們依照罪證數量被判刑,幸運的人被送往生產教育實驗所受感化教育,有些人則被送往綠島新生訓導處十餘年;不幸被判處死刑的玩家,被送至馬場町刑場,生命就此戛然而止。遊戲最後我們一起聆聽了由蔡焜霖前輩演唱的安息歌,一首送給將遠行的難友的歌。有位參與者聽完後被深深觸動,他分享曾經聽過蔡前輩的演講,也提到唱歌是前輩身陷囹圄時鼓舞自己與他人的方式,對於蔡前輩的溫暖記憶猶新。
遊戲中的六位政治犯都有其原型,有舉辦讀書會的校長鍾浩東、無辜被牽連的海軍胡子丹、家庭主婦陳淑端、郵局員工許金玉……玩家在最終討論階段時,能得知作為原型的政治犯們真正的結局,與真實歷史不同的是,遊戲中許多組別最後都被送往綠島,槍決者寥寥可數,對比真實的受難者們,大多數結局唯死路一條。
遊戲結印象束後,玩家們分享最深刻的片段,非檢舉莫屬。很多人一開始對於檢舉充滿罪惡感,捏造莫須有的罪名嫁禍無辜之人,只是為了換取自己的一線生機,使人感到非常愧疚。但漸漸地,筆下捏造的罪名越來越多,便趨於麻木,摒棄了思想才能過得比較輕鬆,甚至覺得為了活下去而出賣他人是必要之惡。在現實中,有人認為若災厄降臨在他身上,他不會選擇出賣他人求生,也有人持反對意見——若所有人都死了,誰能知道他們的故事?總要有人能講那裡發生的事記下來,讓後代得以知曉。
有些人藉著討論機會提出感想,他們對於政治犯們原型故事感到悲傷與不平,在現今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在當時卻能被擴大為數十年的監禁、甚至於失去生命。生於自由的時代,我們僅能以淺薄的文字呈現這些,儘管能感同身受的有限,但已足夠令人震撼,也不禁讓人思考,若真身處那個時代,該是何等惶惑和不甘?遊戲中的失敗與挫折可以一笑而過,但一切真實發生時,我們真能在極端的壓力下堅守底線嗎?又如何能做到在檢舉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時無動於衷?
相信參與者們在本次活動後,都能更加體認到自由與民主的可貴——不會因莫須有的誣陷而獲罪、亦不必時時刻刻為無所不在的眼線擔驚受怕,然而正是如此,我們才更要珍惜民主的可貴,這些幸福得來需經漫長歲月,失去卻只需一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