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7【人權歷史課】轉型正義的回顧與展望|講座側記
2025年2 月26日「轉型正義的目的不為報復,也不只是加害者與受害者雙方的事;是國家暴力永不再犯,並成為整個社會的共同價值及原則。」── 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蘇瑞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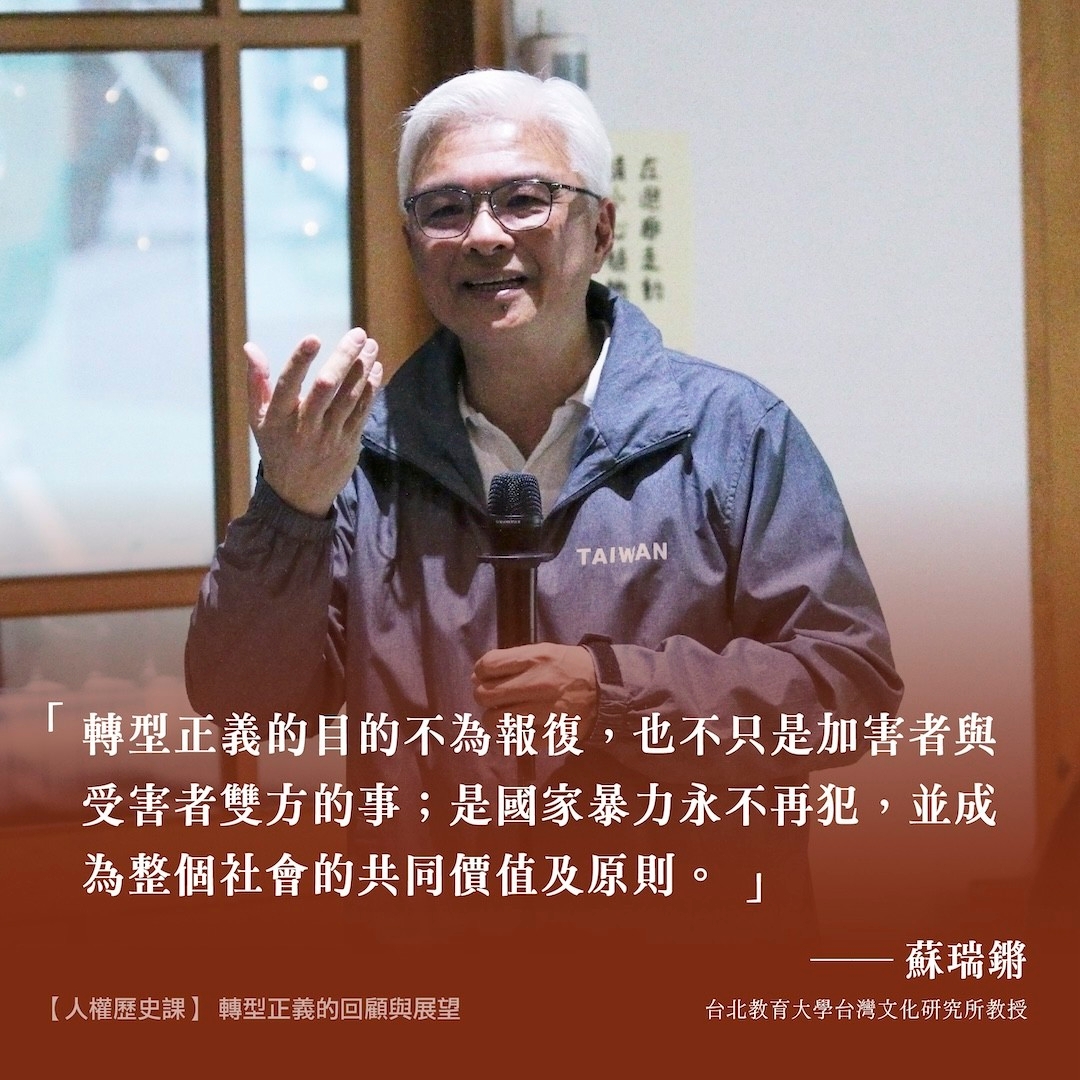
撰文:議題組志工|怡蓉、嘉臨
這場講座由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蘇瑞鏘教授為我們介紹轉型正義的內涵、分析各國作法,也帶我們回顧台灣轉型正義的歷史,跟尚待推動的項目。
何謂轉型正義?民主轉型的最終目標
講者一開始為我們簡介轉型正義的概念。1980年代後期,共產國家陸續垮台,從威權「轉型」民主化後,如何面對威權獨裁造成的傷害,讓「正義」能恢復的政治工程,即轉型正義。這項工程的首要核心是了解真相,尋求正義是和解必要的過程,沒有真相就不會有追求正義的可能,最終目的並非報復,而是讓我們可以記得教訓,不再犯歷史錯誤。
轉型正義主要功能:保障人權與鞏固民主、促進經濟發展、促進族群和諧。且並非僅針對加害者與受害者,而是讓社會大眾體認威權獨裁的迫害是不應該的,讓轉型正義的觀念逐漸變成普世價值。
接著,講者帶我們綜觀許多國家走向民主化後,如何追溯及處理過去的不公義。德國除了東德外,也追溯到希特勒時期的納粹協助者;南非則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交代真相者可能獲得特赦,以鼓勵加害者說出當時的真相;韓國在光州事件10餘年後,全斗煥和盧泰愚兩位前總統即被追究責任,是非常快速實現轉型正義的例子;西班牙則過了32年才通過歷史記憶法,除去獨裁者佛朗哥的雕像。
其他亦有羅馬尼亞、智利等,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處理方式跟時間進程,台灣在這條路上,可以透過討論,建構出屬於我們的轉型正義。
台灣的國家暴力始末
講者蘇瑞鏘教授接敘戰後台灣國家暴力史。二二八事件屬軍事暴力,公賣局查緝私菸演變為官民衝突,國民政府派兵鎮壓造成多人死傷。根據人口學者陳寬政推估,死亡人數約一萬八千至兩萬八千人,而這只是白色恐怖的開始。
自1949年戒嚴後,國民黨以懲治叛亂條例大量抓補人民,縱使1987年宣布解嚴,處置政治犯的法律仍在,如刑法100條、懲治叛亂條例等,直到1992年修正刑法100條,這時才不再有思想言論犯,白色恐怖的威權統治才算結束,然而台灣的白恐受害者評估至少有一萬多人。
雖然白色恐怖表面上看似已經結束,但整個社會仍然存在各種黨國符碼和禁令,如國(黨)歌、國(黨)旗、禁語、黨報書禁等。為鞏固權力,箝制人民自由的國家暴力無所不在,戒嚴日常化,改變了人們的思想價值,甚至難以適應解嚴後的自由。
李登輝接任總統後,台灣終於開始第一波轉型正義工程。國會全面改選、總統民選、二二八事件納入教科書、制定相關賠償條例、成立基金會等,也代表政府向受難者家屬道歉。陳水扁時期,開放大量政治檔案、頒發回復名譽證書、處理黨國符碼等,但朝小野大,政策難以施展。馬英九時期,雖哀悼受害者卻也歌頌加害者,對國家暴力、白恐不真誠又矛盾。近年蔡英文時期,制定成立許多轉型正義相關法律與委員會,如黨產條例、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促轉會、國家人權委員會等,轉型正義才逐漸有新一步的進展。
促轉會解散後,業務移交至各單位並於行政院設「推動轉型正義會報」,持續推動轉型正義,便是台灣目前轉型正義的進度。
未盡之事:我們還有哪些可以努力?
最後,講者分析轉型正義目前尚未完善或需進一步努力的部分。
1.真相的探索
真相回復不僅具有人權價值,也對社會有重大意義。目前已開放的檔案受限於個資的保護,仍有許多內容被遮蓋。應討論國家如何在保護隱私的同時,確保真相釐清。
2.受害者平反的不足
在名詞使用上,賠償象徵國家的認錯,但仍有部分條例名稱採用「補償」的字眼,再再暗示了轉型正義在台灣社會裡尚未完整落實。此外,白恐時期無論財產是否為犯罪所得,皆可能遭國家沒收,目前雖有法源依據,但尚未處理。除了直接的受害者外,許多受難者家屬在經濟、權利或名譽上曾受損害,應將他們納入「受害者」的範疇,並探討救濟方式。
3.加害者究責的困難
加害者究責是爭議最大且進展最少的部分。由於台灣是漸進改革,在真相釐清的階段始終沒有具體點出每起事件中參與威權系統的加害者,相關群體得以透過民主程序繼續掌權,甚至抗拒究責。講者認為,執政者應結合「理」與「力」。在證據與真相日益清晰的背景下,政府應展現足夠的決斷力處理轉型正義。
經由這場講座,我們了解過去國家對人民的迫害,需要透過轉型正義工程對受害者及加害者做出處置,但台灣轉型正義的未竟之事尚多,也還需要社會整體進行更多的討論溝通。冀望在達成和解之後,可以使整個國家記取教訓,永不再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