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今天】——11.20《自由中國》創刊
2024年11 月20日第一,我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促政府(各級的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
第二,我們要支持並督促政府用種種力量抵抗共產黨鐵幕之下剝奪一切自由的極權政治,不讓他擴張他的勢力範圍。
第三,我們要盡我們的努力,援助淪陷區域的同胞,幫助他們早日恢復自由。
第四,我們的最後目標是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
——胡適/《自由中國》創刊宗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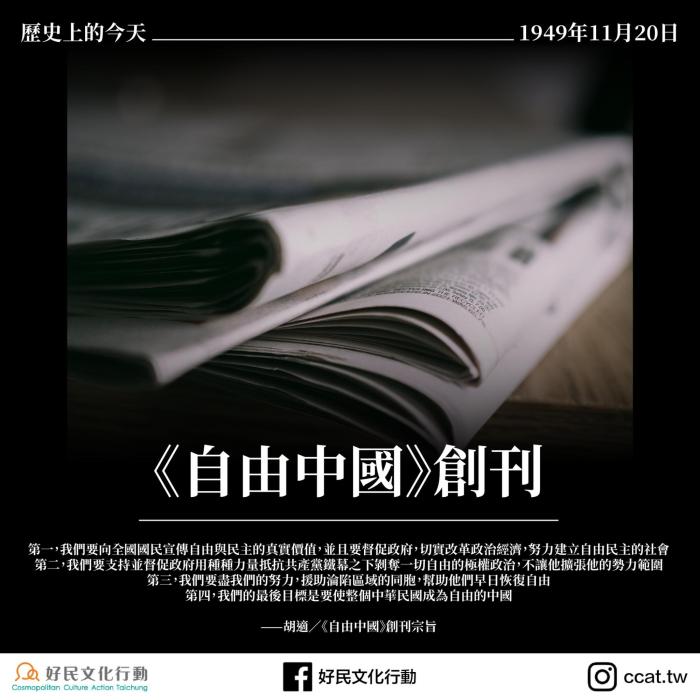
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國》雜誌在臺灣臺北市創刊發行。其中,刊物的發行人 #胡適,便列出上面這四項要點作為《自由中國》的創刊宗旨,聲明要透過自由與民主,與中國共產黨的極權政治進行抵抗,同時也敦促政府落實政治與經濟的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更重要的是——將整個中華民國變成自由的中國。
那個時候,中華民國政府已經因為國共內戰無以挽回的情勢,從中國領土撤退,轉而來到臺灣,而原本預定要在中國創辦發刊的《自由中國》,便也跟著來到臺灣創辦發刊,並宣揚自由與民主的價值。
在1950年代初期的臺灣,《自由中國》與主導政權運作的中國國民黨關係堪稱良好,因此也獲得過贊助與支持。
然而隨著來臺初期,聲稱將為黨內進行檢討改造的國民黨,其「改造」結果卻是形塑出一個更加獨裁且鞏固權力的威權體制,這便引起了黨內自由派人物的諸多不滿,而《自由中國》與國民黨政權的關係也逐漸變得緊張。
同時,由於韓戰的爆發,美國在利益的考量下重新開始支持蔣介石,政權當局原先希冀透過自由派人物來改善自身形象、藉以持續爭取美國援助的必要性,也就因此下降,繼而更加有恃無恐。
自此開始,《自由中國》的發行內容,也就慢慢從擁戴蔣氏政權、抨擊共產主義的方向,轉變為批判臺灣社會內部的政治問題,而在白色恐怖如火如荼進行的當前,《自由中國》儼然變成檯面上唯一挑戰著政權當局敏感神經的異音。
例如1956年10月31日,適逢蔣介石的七十歲生日,《自由中國》雜誌也順勢推出〈#祝壽專號〉,並邀請知識分子撰寫文章,對當局提出建言。
可想而知,其內容無非是對蔣氏政權極盡嚴厲的批判,包含胡適的〈#講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以及 #徐復觀 的〈#我所了解的蔣總統的一面〉等,諸多內容也被當局軍方指為「#毒素思想」。
1957年,《自由中國》又推出一系列「#今日的問題」社論,針對當前局勢、社會議題、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問題,做了全面性的檢討。
其中,#殷海光的〈#反攻大陸問題〉一文,極力規勸政府當局,不要再將反攻大陸作為短期目標,以避免在臺灣有太多政策都屬於過渡性質,不求徹底或永久,進而更主張「#實事求是,#持久漸進,#實質反共」,但這樣一番從今天看來頗為中肯務實的言論,也被當局指為「#反攻無望論」。
到了1959年至1960年,雙方之間的衝突變得更加尖銳。由於當時蔣介石已經連續擔任兩屆總統,理應當不能再繼續連任,但不願釋放權力的他,遂透過一連串的手段,試圖讓自己得以接續連任。
如此作為也已經違背了中華民國憲法的精神,自然讓這些知識分子也看不下去,隨即發表多篇文章加以抨擊反對,並言明:「民主政治是今天的普遍要求,但 #沒有健全的政黨政治就不會有健全的民主,#沒有強大的反對黨也不會有健全的政黨政治。」
由此,這些知識分子也意識到,必須要成立一個強而有力的監督黨,與執政黨形成有效的抗衡,才能避免其繼續坐大;《自由中國》的主要編輯成員雷震,也開始多方奔走,企圖結合臺灣各界人士共同組成反對黨。
而隨著反對黨的組成與結構愈臻成熟,這群知識分子對政權當局所造成的威脅也等同更加迫切,後者也開始透過《中央日報》等主流媒體的資源,指稱雷震等人組建新政黨的舉動,是為配合中國共產黨的「統戰政策」,企圖「造成臺灣的混亂」以及「顛覆政府」的陰謀。
到了這個地步,曾經以和共產主義對抗,標舉自由民主價值,而受到公權力支持的這群知識分子們,也開始被貼上了匪諜的標籤。
1960年09月01日,殷海光的文章〈#大江東流擋不住〉在《自由中國》發表,主張新政黨的籌組,對國家所產生的益處,同時也嚴詞抨擊中國國民黨對其所做的抹黑栽贓,以及其傲慢獨裁的態度。
最後,殷海光強調,民主政治真正實行,才能結束獨裁者的專斷和控制,更以「#大江總是向東海奔流的」,來比喻人民對自由、民主以及人權保障的渴望,並非「#霸佔國家權力的少數私人」所能永久阻遏。
〈大江東流擋不住〉刊登後,又過了三天,雷震等人便遭到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以「涉嫌叛亂罪」的名義逮捕,並且在軍事法庭上,以「為匪宣傳」、「知匪不報」等罪民羅織,遭判處徒刑,而《自由中國》當然也難逃停刊的命運。
雖然《自由中國》在1960年隨著雷震等人遭到拘捕而停刊,但真的就像殷海光所言,滾滾滔滔的大江東流,就算一度被迫壓抑,不得不隱藏潛伏,最終還是會衝破獨裁政權試圖一手建立的藩籬。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1980年代百花齊開、大鳴大放的 #黨外雜誌,或許就可以視為這股精神的體現,而中國國民黨曾經想要阻攔的人民籌組新政黨的意圖,也在1986年民主進步黨的成立之後,跟著一起被推翻。
另一方面,當我們把時間推移到現在,更可以意識到,臺灣在國際之間的關鍵性與重要性,也變得更加明確,由此看來,當我們繼續把自己看作「自由中國」,甘願深陷在「自由中國」與「共產中國」的角力之中,就顯得過時且不切實際了。
如果當年殷海光曾在〈反攻大陸問題〉一文中,呼籲政權當局「實事求是」,那麼此時此刻,屬於臺灣的實事求是,就是讓臺灣真正以「臺灣」這個名字,站在國際的舞台上,而不是把自己指稱成另一個中國,在面臨中國共產黨的侵略時,掉入內戰的脈絡裡。
由於前輩們的努力,現在的臺灣,已經是一座落實自由民主的島嶼,那麼我們就更應該承繼這份為了守護自由與民主,因而努力不懈的精神,把臺灣進一步變成一個正常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