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今天】—1018 楊逵生日
2024年10 月15日楊逵不只是一名作家,更在台灣遭受殖民政權統治,以及威權政府的戒嚴體制之下,積極關懷台灣社會,透過社會運動的參與以及文學的書寫,追求自由、民主、反抗獨裁霸權、無歧視與壓迫的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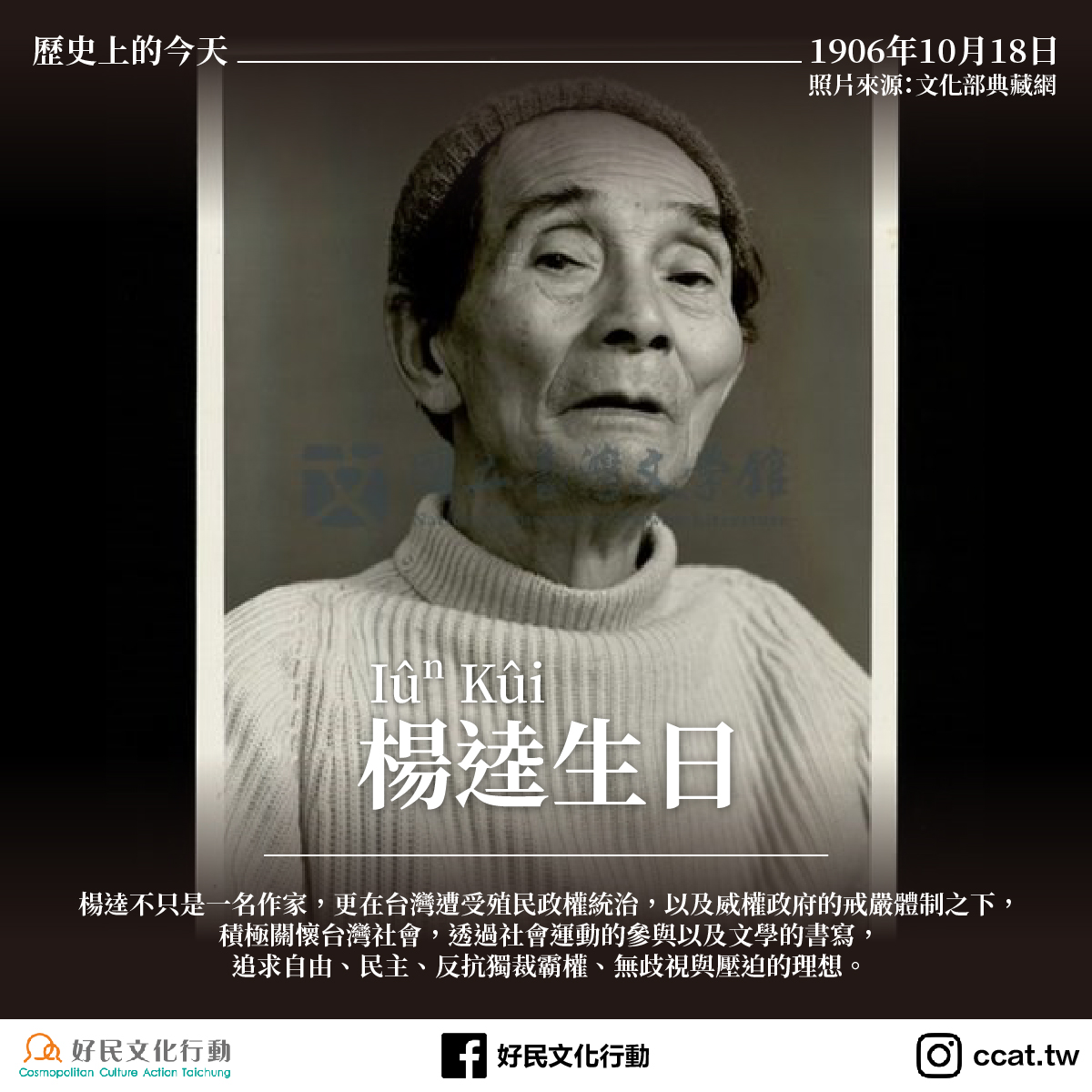
【歷史上的今天】1018—楊逵生日
楊逵(Iûⁿ Kûi),本名楊貴,1906年10月18日生於臺南州大目降街(今臺南市新化區)。楊逵不只是一名作家,更在台灣遭受殖民政權統治,以及威權政府的戒嚴體制之下,積極關懷台灣社會,透過社會運動的參與以及文學的書寫,追求自由、民主、反抗獨裁霸權、無歧視與壓迫的理想。
▶早年生活與關懷視野的啟蒙
由於幼時家境貧困,加上體弱多病的關係,楊逵直至十歲左右方進入新化公學校就讀。身材瘦弱的他,時常被同學作弄,一方面拿他的名字「楊貴」作文章,以「楊貴妃」揶揄他,又或者嘲笑他的外表,喚他為「阿片仙」。孩童直率的殘忍與惡意,在年幼的楊逵心裡種下一顆顆種子,他因此並不喜歡「楊貴」這個本名,對自己所面臨的強者欺凌弱者的環境,甚早便已有深刻的認識。
另一方面,在1915年發生的噍吧哖事件中,楊逵的兄長被強迫前往協助日方運輸鎮壓所用的軍火,當時年幼的楊逵也透過門縫,看到外頭殖民政權所出動的大量武裝鎮壓部隊,帶著肅殺的氣息浩浩蕩蕩從家門前經過;加上在村民與家人的口耳相傳中,繪聲繪影轉述的日軍對涉事者所進行的行刑過程,對殖民政權的憤怒,以及對自身民族所遭遇的悲劇,讓楊逵日後的成長過程中,逐漸構築出反抗的精神與信念。
楊逵於1922年考入臺南州立第二中學校(今臺南一中),1924年,一方面不願屈從於長輩安排的傳統婚姻,另一方面又力圖拓展自身的視野,便從第二中學校輟學,前往日本留學。
楊逵考入日本大學專門部文學藝能科夜間部,從此開始白天打工賺取學費與生活費,晚上勤學苦讀的日子。這段留日的歲月裡,他也組織文化研究會,參與當地的勞工運動、政治運動,並透過文章發表,表達自己對社會運動與勞工處境的看法,如刊載於雜誌《號外》第一卷第三號的〈自由勞動者的生活剖面——怎麼辦才不會餓死呢?〉。
1927年9月,楊逵回到台灣,參與當時由台灣農民組合所發起的農民運動,而也是在這段期間,他結識了葉陶,兩人最終在1929年結為連理。
▶送報伕:左派運動的實踐以及與文學的結合
楊逵自青年時期便積極參與頗具左翼色彩的勞工運動與農民運動,自己也經歷過受雇主壓迫的勞動者的生活,這些經歷後來逐漸具現於他的文學作品上。1934年,他的小說〈送報伕〉入選東京「文學評論」第二獎,首獎從缺。
〈送報伕〉描述一名臺籍青年「楊君」前往東京謀求發展,卻遭受到雇主的壓榨欺騙,面臨種種打擊,所幸他目睹同為送報伕的同伴們團結罷工,迫使雇主讓步,最終獲得工作環境與待遇的改善,在小說的最後,楊君帶著這些抗爭經驗,踏上返回故鄉的道路。〈送報伕〉全篇作品帶有濃厚的左派精神,更彷彿楊逵的一篇小型自傳,其中「對雇主反抗,迫使其向勞工階級妥協」,以及「帶著成功的抗爭經驗返回故鄉」的情節安排,更帶著當時左派青年堅毅浪漫的理想色彩。
也就是在這一年5月,臺灣文藝總聯盟也在台中成立,楊逵擔任其機關雜誌《臺灣文藝》的編委,只不過由於思想路線的不合,楊逵最終離開《臺灣文藝》,並自創刊物《臺灣新文學》。至1936年至1937年間,日本殖民政權對台灣社會的控制愈加嚴苛,臺灣文藝聯盟遭到解散,《臺灣文藝》和《臺灣新文學》也陸續遭到停刊。
▶鵝媽媽出嫁:共存共榮的荒謬與絕望
中日戰爭爆發後,楊逵一度遭到逮補,之後出獄,在友人的資助下開闢「首陽農場」,以「首陽山上,義不食周粟」的典故,宣達自己對殖民政權的不認同;同時也持續發表文學作品,包含1942年發表於《台灣時報》274號的〈鵝媽媽出嫁〉。
故事分為林文欽與敘事者「我」兩個主線,以敘事者的觀點,描述堅守馬克思思想的友人林文欽,企圖透過和平、非暴力的協調方式,將自家擁有的龐大祖產投入到全體共榮的經濟計劃中,沒想到最後卻因為積欠債務,遭至家破人亡,自己也在窮困潦倒中迎來夭亡的命運;另一方面,敘事者經營園圃、種植花草,養了一群鴨鵝,卻在和醫院院長交涉的兩百株龍柏的生意過程中,遲遲沒有意會到院長對家中飼養的母鵝的偏愛,而頻頻遭受刁難,最後終於在旁人指點下,將孩子們心愛的「鵝媽媽」給「嫁」到院長家,自此拿到不斷被拖欠的費用。
「『這就是共存共榮。』種苗園老闆又說了。大東亞戰爭就以『共存共榮』為標榜,連這位鄉下人也學會了這一套。」作為雄壯的口號,在戰爭期間大肆放送的「共存共榮」,說穿了在看似美好的外衣下,本質仍是強者對弱者的欺凌;在楊逵的作品中,更諷刺地透過林文欽和敘事者的不同下場,對比出渴盼認真實踐「共榮經濟理念」者的注定失敗,以及共同虛矯地串演出「共存共榮」者,因而僥倖生存的悲哀。
在太平洋戰爭打響的第二年,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推行,各地都在舉報「間諜」與「非國民」,意識形態被高度審查的期間,公開發表的〈鵝媽媽出嫁〉,豪不客氣指出殖民政權堂堂正正祭出的「共存共榮」的口號,背後所夾帶的荒謬與絕望。
▶和平宣言:全世界最貴的稿費
終戰後,楊逵與葉陶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的清算過程中雙雙被捕,又於8月獲釋。到了1949年,楊逵有鑒於當時在中國愈演愈烈的國共內戰,因而在上海大公報發表〈和平宣言〉:
「台灣……深恐戰亂蔓延到這塊乾淨土,使其不被捲入戰亂,好好的保持元氣,從事復興。」楊逵在文中極力呼籲,以台灣作為和平建設的示範區,避免遭受國共戰亂的波及,也進一步提出和平建設的具體方針,以還政於民、保障人權、釋放政治犯、停止政治性逮補、打破經濟不平等、實施地方自治等作為訴求。文末,楊逵更主張道:「我們相信,以台灣文化界的理性結合,人民的愛國熱情,就可以泯滅省內省外無謂的隔閡。我們更相信:省內省外文化界的開誠合作,才得保持這片乾淨土,使台灣建設上軌,成個樂園。因此,我們希望,不要再重武裝來刺激台灣的民心,造成恐懼局面,把此一比較安定乾淨土以戰亂而毀滅。」
這是在歷經二二八事件以及隨之而來的暴力性鎮壓,以及自身遭受逮捕後又被釋放後的楊逵,對於當下的台灣所做出的呼籲,然而這樣的舉動,使得他再度遭受逮補,其後被判處十二年的有期徒刑,送往綠島服刑。
在過去,推動農民與勞工運動的楊逵,固然也是經常被殖民政權逮補、審判、監禁的對象之一,而根據張良澤的記憶,在他與楊逵對談的過程中,也聽楊逵講述過當時批判政府可能遭至的後果。楊逵提到,日本帝國再嚴酷,也是依法辦罪,如果是以演說、撰寫文章來攻擊政府的話,最重會被判坐牢二十九天;只不過,回到「祖國」的懷抱以後,法治基礎變得不明不白,而他光是因為一篇不過五、六百字的〈和平宣言〉,就被關了十數年。
▶春光關不住:慘白水泥塊下的盛放玫瑰
在綠島服刑的這段期間,楊逵也持續投入創作,並將作品發表於《新生活》壁報與《新生月刊》,包含後來改名為〈壓不扁的玫瑰〉的〈春光關不住〉。
表面上,〈春光關不住〉依舊以直白的筆調,明確批判二戰時期的台灣,在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號召下所遭遇的苦難,又以盟國空襲轟炸後,被水泥塊壓住的玫瑰花苞,暗喻台灣人民火熱而堅韌的心,最後更透過「將玫瑰植入黃花缸(崗)」的寓言,作出人民共同集結的呼求。
但有許多人也注意到,〈春光關不住〉或許不單只是一篇批判「日人對台人壓迫」或顯示「台人對日人抵抗」的小說而已,畢竟〈春光關不住〉被書寫、刊登的背景脈絡,是楊逵因為一篇以溫和訴求為核心的〈和平宣言〉,而被送往綠島服刑多年,他所面臨的不再是那個只會「居留二九工」的殖民政權,而是一個更腐敗、蠻橫而不講理的獨裁政權;是以,我們不妨回頭詢問,那個在故事中不斷壓迫欺凌人民的「軍閥」究竟是誰?而壓在玫瑰上的水泥塊,象徵的又是什麼呢?
倒不如說,始終與普羅大眾站在同一陣線的楊逵,所立足的是一個更高的視野,他真正要批判的,是所有壓迫、剝削人民的強權與暴政,無論這樣的政權來自哪一個國家,都會是他加以批判的對象,只不過當時身陷囹圄,又是在戒嚴所造成的白色恐怖氛圍下的楊逵,仍舊以「日本帝國」作為一個惡人的臉譜,藉以讓他的這套「強權壓迫弱者、弱者抵抗強權」的敘事,可以背堂而皇之地通過軍警的審查、發表到月刊上——而誰能說它不是一個最正確的敘事呢?但在當時,又有誰能更進一步解讀這份幽微的心緒呢?
▶用鋤頭在大地上寫詩:東海花園與台中文化城願景
楊逵在1961年出獄回到台灣,並在東海大學對面購置荒地,闢建東海花園。東海花園在1970至1980年代,因為楊逵而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化地標與文學教育空間,更讓不少人前往朝聖,對楊逵而言,東海花園則是他希冀促成臺中「文化城」的起點,拋磚引玉,讓東海花園可以有更豐富的活用。
1985年03月12日,楊逵在女兒楊碧的家中離世。不僅在稿紙上勤懇地筆耕,同時也「用鋤頭在大地上寫詩」,楊逵對人權與人道主義的關懷,寫成了文學,也實踐在他窮盡一生投入參與的社會運動與文化推廣。
時至今日,楊逵生前未竟的那個,起造臺中文化城的遺志,雖然依舊被一群關懷台灣的土地、歷史與文化的人們記持著,歷經兒子楊建、孫女楊翠長期的奔波爭取,但面臨當今土地開發利益的複雜關係,是否真的有落實的一日呢?遙想這片苦心赤誠傳承至今,卻也可能被無奈剝削,令人不勝唏噓。

